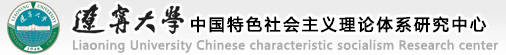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其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医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能够“药到病除”,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更是“灵丹妙药”。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带给发达国家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停滞和混乱。
(一)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
新自由主义依赖数学工具,反对经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希望以实证的方式客观地分析经济问题。它也以此为标准并以经济科学自居,而将其他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伪科学”。但是这种貌似客观的经济分析工具却落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这就导致其分析只能是脱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其政策建议只能是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不仅是唯心的,而且是机械的。从休谟开始,人性、个人动机就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和自利选择原则在边沁那里开始成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信奉的教条。到了19世纪末,边际学派进一步将物品的效用完全变成了一种脱离客观价值基础的个人主观心理体验,经济学就成为一个以心理解释心理的“科学”,任何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都被归结于人的行为动机,而人的行为动机又归结于人的本性。个人主观心理体验就如同一个大筐,可以将任何解释不了的经济社会现象装入其中。
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机械的。它不仅仅将所有经济现象的发生归结为人的动机,更是将人的动机机械地固定为“利己主义”;除了机械地看待人的本性,它同样机械地认识客观的自然。这两方面集中的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
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命题,一是人是自利的,二是人具有无限的理性,三是人具有完全信息。虽然在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修复中这些命题被不断地放宽,但其核心——人的自利性假设始终没有改变。“经济人”假设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具有“理性”思维和“利己”观念的个体。受“利己”观念的指引,“经济人”基于“理性”算计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毫无关系。至于人是“理性”和“利己”的这一前提假设,则被归结于人类的本性。正因为人是“利己”的,所以人必定“欲望无限”,所以人所面临的资源必然是稀缺的。
这些观点似乎经得起当前现实的检验,但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迷惑性所在。并不是人的本性天然如此,而是在现有生产关系中人们恰巧表现出来这样的本性。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早已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前提是客观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独立和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的思想意识,进而决定了其行为。
新自由主义貌似“准确”地把握了人的本性,貌似“客观”地看到了自然资源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但它忽略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具有一般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造成资源(更准确地说是产品)的相对稀缺,视为永恒存在的自然状态。人的本性和资源对生产的限制并不像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从人的几何级数增长与产品的算数级数增长的矛盾出发,论证了资源稀缺的正确性,但我们只要置身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在地广人稀的原始社会,人类面临的是资源“稀缺”还是“丰富”呢?在衣食难以保证、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当然是面临稀缺;地广人稀又何来稀缺呢?因此所谓的稀缺与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同时,从私有制的发展来看,它并不是出现在早期的原始社会,恰恰相反是出现产品过剩以后,才出现了部落首领侵占产品的现象。因此,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直接影响着所谓的稀缺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提出的“稀缺性”造成了“私有制”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科斯以后的西方产权理论进一步延续了这种逻辑,他们提出随着某件物品价值的提高就应当对其建立产权,而物品价值的提高正是因为它的日益“稀缺”,由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循环论证中。显然,正确的命题应该是“私有制”造成了“稀缺”。
实际上,人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主体,又是社会关系形成与创新的主体。作为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社会的人,是受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着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另外,“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一切已亡故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貌似严谨科学的数学逻辑背后隐藏的是机械、主观的理论逻辑,是脱离客观现实的理论假设。它无法对经济现象作出真正准确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就像面对此次经济危机一样,它不但无法预测,而且究其原因也始终只能追溯到“监管乏力”和“贪婪、自私”的人性。当然,这也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必然会一次次走向失败的根源。
(二)虚伪的价值中立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强调价值中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这个问题上鲜明提出“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及其结论”。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做到了价值中立,而又能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呢?
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看,无论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还是“华盛顿共识”,都涉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市场、放松监管、打压工会、减免企业税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等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在为谁谋利呢?芝加哥学派除了论证减少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之外,还指出“垄断是不重要的或短暂的”,“税收制度应该被用来提高收入而不是收入再分配”,这又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来看看发生在美国的实际情况。
美国在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的30余年里,“放松政府对交通、通讯和电力等部门的管制,大幅降低了这些部门的工资;放松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制,加剧了资本外流和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竞争;实施私有化公共服务后,公共服务就转到了由私人承包企业的低工资雇员的手中;为了降低失业率而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反而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削减社会计划,降低了工人的‘社会工资’,这种‘社会工资’在以前能加强工人的议价能力;减少对企业和富人的征税,加剧了税后不平等性;企业和政府联手对抗工会,严重破坏了工人的议价能力,这可能是最明显的;企业转向雇佣临时工和兼职员工,使得就业工资降低;大型企业之间无约束的竞争对工资也造成了压力,最后,CEO的市场化导致CEO工资扶摇直上,从1982年是一个普通工人工资的42倍,一路飙升到2005年的411倍”。
除了“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主张外,“人权”、“自由”和“公平”也是新自由主义常常挂在嘴边的概念,但是“他们毫不吝惜赐给弱势群体以话语权利,至于支撑话语权利的经济权利(这才是人权和公平的基础和根本),则是不能也不愿给予的”。在自由平等和价值中立背后,新自由主义所信仰的实质上是资本和金钱的强权。换言之,它所谓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和“金钱”的自由,拥有了资本和金钱也就拥有了最大的自由,而且这样的自由是公正的和合乎“自然”法则的。
新自由主义虚伪的价值中立在其自身的逻辑体系中也是站不住脚的。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人是自利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资源是有限的,那么资源的配置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呢?答案是货币。因为人对某物的评价越高,他给出的价格也会越高,资源配置给评价最高的人就达到了最优的配置。
曼昆在他盛极一时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你口干舌燥——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脱水。你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而且店主人认为乘人之危是不道德的,因此,他不会比上一周多收你一毛钱。但是,……水卖完了。你继续当你的顾客,并最终发现了面目狰狞的价格欺诈者。他上周卖1美元的一瓶水现在是‘可耻’的价格……但如果不是他要价20美元,他的水就卖完了。正是这个价格欺诈者的‘趁火打劫’救了你的孩子。”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即高价格最优地配置了资源。但是,他们故意“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用来选择资源的选票——货币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对资源有最大需求(如上面那位需要水救活孩子的家长)并不一定有足够的货币选票来表达他的偏好,而他的需求就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化面前变成了不合理的要求,成了非帕累托最优。可见,即使在新自由主义自身的逻辑之下,它所谓的价值中立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鲜明地站在了货币和资本的立场之上,当然它披上了“皇帝的新装”。
新自由主义者毫不隐讳地宣称:因为资源有限,最优的权利分配职能是将权利向能生产更多财富的人倾斜。这样,财富拥有者的利益优先权就披上了所谓的“效率优先”原则的“马甲”。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和法律只代表了资本强权者的意志,仅仅是他们统治的工具,绝不像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弱者权利的保证书。当前,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部分地方政府的眼中,能创造GDP、能上缴税收的企业,无论它是破坏生态,还是侵占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权力就沦为他们的利益同盟,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优胜劣汰”的丛林逻辑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形式是沿着物理主义道路走向主观和机械的话,那么它的内在逻辑则是沿着生物进化道路走向纯粹生物的野性。新自由主义崇尚竞争,崇尚最大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崇尚“优胜劣汰”的丛林逻辑。“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经由马尔萨斯进入了新古典的理论体系,进而发展为新自由主义的逻辑。
新自由主义将“优胜劣汰”的丛林逻辑直接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不仅仅在理论逻辑中不能自圆其说,更是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底线,造成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生物的“优胜劣汰”是异类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自然环境对不同种类生物的选择,而非同类间的践踏。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内,异类生物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往往表现为你死我活式的生存竞争关系。优胜劣汰是这种生存竞争自然规律的归纳。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将这种竞争不加限制地扩展至人类社会,在逻辑上显然夸大了竞争机制的内涵。物种内部的关系除了竞争关系外,还有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即使在动物中也不鲜见,如集体迁徙途中大河马对小河马的保护,蜜蜂在受到威胁时会牺牲自己来保护种群等等。
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优胜劣汰”被演化为“赢家通吃”,这更是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底线。达尔文曾经指出:“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重要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重要差别之上的一个差别是道德感或良心……人在天地间的一切物体之中是唯一配得上称为有道德性的生物这样一个事实就构成他和低于他的各种动物之间的一切区别之中的最大区别。”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是社会性动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无论他表现得多么自私,在人的天性里都有着某种天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这类天性就是怜悯或同情。
优胜劣汰是生物竞争的事实,但是这种结果上的事实并不能成为优胜劣汰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的依据。“优”与“劣”是由制度来认定的,人能够主动建构社会环境,通过人类对制度环境的安排来决定社会环境的“适与不适”,进而能够影响优劣的判断。如果把优胜劣汰作为人类竞争的规则,那么它在实际运行中就常常会被强势利益阶层置换成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利益阶层利用这样貌似合理的规则,打压、排斥乃至淘汰因制度造成的弱者,这样的规则作为人类社会的竞争尺度在道德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网络编辑:岚河水
《管理学刊》2012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3-4-18 13:41:59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